何以“傳華夏”?


——周文化基因傳承變異的原理-操作機制探析
周文化基因跨越三千年的生命力,決非源于僵化教條,而在于“原理層內核恒定—操作層實踐迭代”的動態平衡機制。這一機制既守護了文化認同的連續性,又賦予文明適應不同歷史情境的靈活性,最終塑造了中華文明獨特的氣質與韌性。本文從傳承內核、變異路徑、驅動邏輯與現代啟示四個維度,系統闡釋這一機制的運行規律,并揭示其對理解中華文明韌性與現代轉型的深刻啟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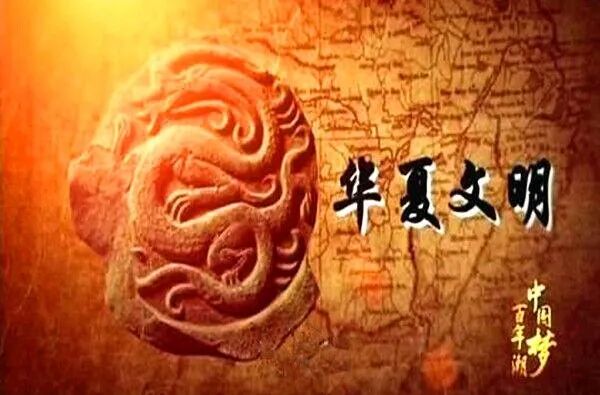
一、原理層:文明延續的“生成性內核”
周初的文化基因建構,核心價值并非制定封閉規則,而是確立了三個具有可衍生、可擴展特性的生成性內核——它們如同文化基因的核心序列,歷經時代變遷始終未變,為中華文明提供價值錨點與意義框架,構成穩定的“意義之三角”。
1. 倫理秩序:基于人倫的共同體建構原理
周文化基因完成從商代“神權至上”到“人倫本位”的范式革命,通過宗法制度將社會凝聚力錨定于君臣、父子、夫婦等倫理關系,構建“家國同構”的秩序模型。這一原理的精髓是“以倫理整合社會”:后歷經孔子“克己復禮為仁”的“內在化”(將倫理轉化為道德自覺)、董仲舒“三綱五常”的“系統化”(轉化為帝國規范),直至宋明理學“天理即人倫”的“哲學化”,操作層具體規則不斷流變,但“倫理作為秩序基石”這一核心原理,如同定海神針,貫穿古今,成為中華文明最鮮明的標識。
2. 德治民本:政治合法性的價值圭臬
“敬德保民”的理念,既見于傳世文獻(《尚書·康誥》:“惟乃丕顯考文王,克明德慎罰,不敢侮鰥寡”,孔安國傳、孔穎達疏《尚書正義》,中華書局1980年版),亦有出土銘文佐證——大盂鼎銘文載“今我唯即井(型)稟于玟王正德”【6】,強調統治者需效法文王之德;逨盤銘文“用配乃辟,踐堇大命,享孝康娛,屯右廣啟,廣奠周邦,綏愛四方”【6】,凸顯“以德固邦、以民為本”的治理邏輯。這一原理為權力劃定倫理邊界:政治合法性既源于“天命”,又依賴統治者的德行與對民眾的關懷。它成為后世評價政權的終極標尺:漢初“休養生息”、唐太宗“水能載舟”、清代帝王“勤政愛民”的標榜,無論實際成效如何,都是對這一原理的呼應。即便歷史中存在實踐與理想的背離,“德治民本”始終是政權自我辯護與批判反思的價值依據。
3. 禮樂文明:和諧秩序的符號化表征
“禮”與“樂”并非單純的儀式或藝術,而是塑造秩序與和諧的文化符號系統:“禮”通過規范行為“別異”,確立社會差序;“樂”通過情感共鳴“和同”,凝聚群體認同。后世雖不再拘泥于周代“籍田禮”“大射禮”等具體儀軌,但“禮”的精神滲透于官儀民俗(如傳統婚喪禮中的“敬親”內涵),“樂”的教化功能傳承于漢代樂府的采風以觀民情、唐代雅樂的制定以和朝序、宋代書院的融樂以修身心。三者共同鑄就了中國人對“何為文明”的深層認同。

二、操作層:應對挑戰的“三次關鍵變異”
原理層的恒定,為操作層靈活變異提供了根基。周文化的活力,正體現為操作層為回應環境挑戰而實現的三次關鍵性轉向——呈現“良性—利弊交織—僵化(適應性退化)”的遞進軌跡,且每次變異均直接作用于“原理層—操作層”的動態平衡:良性變異鞏固平衡,利弊交織變異傾斜平衡,僵化變異(適應性退化)則打破平衡,導致文明從“適配時代”轉向“失配發展”,深刻影響文明走向。
1. 春秋戰國:從“制度之禮”到“精神之仁”的哲學升華(良性變異)
面對“禮崩樂壞”的失序,以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者未拋棄周文化,而是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:孔子將“禮”的根基從外在儀軌轉向內在“仁”,提出“人而不仁,如禮何?”(楊伯峻《論語譯注》,中華書局1980年版),使倫理成為主體的道德自覺;孟子則將“保民”具象化為“制民之產”的“仁政”藍圖(焦循《孟子正義》,中華書局1987年版)。
此次變異中,操作層始終圍繞“激活原理內核”展開,讓周文化從封建制度升華為具有普遍倫理意義的哲學體系——既未偏離“倫理秩序”“德治民本”的核心,又讓原理層適配“亂世求治”的時代需求,鞏固了“原理—操作”的平衡,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思想根基。而這一轉化的歷史價值,恰在后世得到印證:北宋張載所言“為往圣繼絕學”,其“往圣”脈絡正包含兩層核心——一是開創周文化“德治民本”“禮樂文明”的周公等周初圣王(原理層的奠基者),二是接續這一脈絡、激活原理活力的孔孟(此次良性變異的主導者)。孔孟的努力,讓周文化從“周代專屬制度”成為儒家道統的“源頭學問”,也為后世“繼絕學”提供了核心思想載體。
2. 秦漢至隋唐:從“貴族倫理”到“帝國綱常”的制度化綁定(利弊交織變異)
大一統帝國的治理需求,推動操作層與皇權制度深度綁定:宗法從“家國一體”轉向“以皇權為頂點的絕對綱常”(如《白虎通義》將“君為臣綱”列為“三綱”之首),禮樂從“貴族與民眾共享的符號”變為“彰顯帝國威嚴的工具”(如漢代叔孫通制定朝儀、唐代《大唐雅樂》以“萬國來朝”為主題的宮廷樂舞體系)。這一變異的“利”在于:讓原理層適配“大一統治理”新形態,鞏固國家統一;“弊”則在于操作層開始偏離原理初心——“德治”重心從“約束君主敬德”轉向“要求臣民忠順”,“民本”從“統治者的責任”弱化為“穩定統治的手段”,“原理—操作”的平衡首次出現傾斜,原理層的價值內涵開始被窄化。
3. 宋至明清:從“實踐智慧”到“道德絕對”的僵化變異(適應性退化)
伴隨科舉制完善與士大夫階層固化,操作層徹底走向教條化,不僅自身“適應性退化”,更反向窄化甚至扭曲原理層的解釋空間:宋明理學將倫理綱常升華為壓制人欲的“絕對天理”(朱熹提出“存天理,滅人欲”,《朱子語類》卷十三,中華書局1986年版),消解了周初倫理“以人為本”的彈性——原本“以倫理整合社會”的原理,異化為“以倫理壓制人性”的工具;“崇古”從“托古改制”的靈活策略,異化為“言必稱三代”的復古主義;對“秩序”的追求更異化為“以穩定壓制變革”(如清代閉關鎖國政策、對西學的排斥)。
至此,操作層不再是“原理的適配者”,反而成為“原理的禁錮者”——周文化“因時損益”(《論語·為政》:“殷因于夏禮,所損益,可知也”,楊伯峻《論語譯注》,中華書局1980年版)的精神被掏空,“原理恒定—操作迭代”的動態平衡徹底打破,中華文明逐漸呈現“保守傾向”,本質是操作層僵化導致的“文明適應性退化”。

三、驅動邏輯:時代壓力與解釋權博弈的雙重
作用操作層的變異并非隨機,而是“外部時代挑戰”與“內部解釋權博弈”共同作用的結果,兩者的互動直接決定變異的性質與方向,構成周文化傳承與變異的核心動力。
1. 時代挑戰:變異的“壓力源”
不同歷史階段的核心矛盾,為操作層設定明確變異方向:春秋戰國的“失序危機”(分封制瓦解、諸侯爭霸),要求文化從“西周制度工具”升華為“凝聚社會的精神內核”,催生“哲學升華”;秦漢的“大一統需求”(疆域擴大、治理難度提升),要求文化轉化為“中央集權的治理術”,推動“制度綁定”;宋明的“內部維穩訴求”(宋代防藩鎮割據、明代防宦官專權、清代防漢人民族意識),傾向于用“思想統一”鞏固統治,導致“教條化”。這三次轉向,本質是文化為應對“生存挑戰”而做出的“適應性選擇”,但選擇的結果(良性/利弊交織/僵化),則取決于解釋權的歸屬。
2. 解釋主體:變異的“掌舵者”
解釋主體的身份與立場,直接決定其對原理層的“激活”或“扭曲”:
思想家(孔孟)主導時,以“回歸原理初心”為目標——通過重構操作方案(如“仁化禮”“仁政”)激活內核活力,讓原理層適配時代卻不偏離本質,形成良性變異;
政治家與儒者合流(如董仲舒與漢武帝、程朱理學與后世帝王(明太祖、清康熙帝)的推崇相結合)主導時,以“服務權力”為核心——既在形式上保留原理層的價值符號(如“德治”“民本”的表述),又在實質上改造操作規則以強化皇權(如“天人感應”約束君權的同時,“三綱”固化等級),形成利弊交織變異;
固化的士大夫階層(如明清科舉士人)主導時,以“維護階層利益”為首要——絕對化、教條化(如“八股取士”限定經典解釋),通過“壟斷文化解釋權”鞏固自身地位,最終導致僵化變異與適應性退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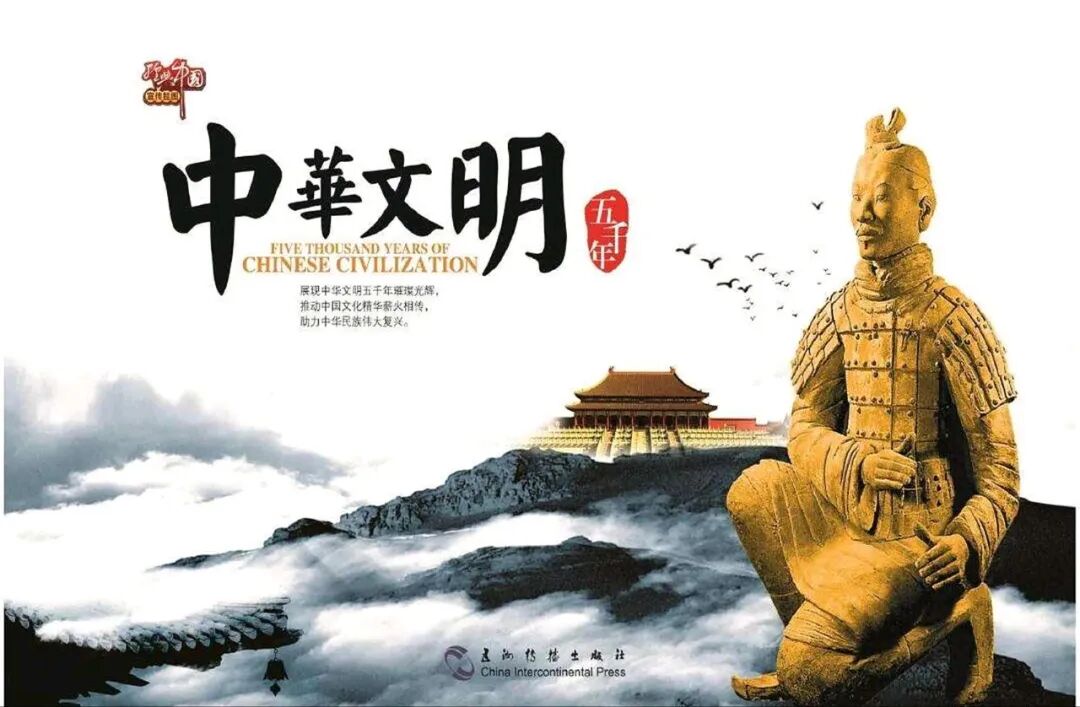
四、現代啟示:“守正創新”的具體路徑與文明活力激活
周文化的當代價值,絕非“復古”(回歸操作層的舊形式),而在于重振“守正創新”的核心智慧——“守正”是堅守原理層的“價值本質”,而非“操作形式”;“創新”是重構操作層的“現代表達”,而非“背離內核”,最終重建“原理—操作”的動態平衡,激活文明生命力。
1. “守正”:守住原理層的價值本質,剝離操作層的僵化形式
這種“守正”,本質是對張載“為往圣繼絕學”精神的當代呼應——張載所繼的“絕學”,核心正是“往圣”傳遞的文化內核:既是周初圣王(周公等)確立的“德治民本”“倫理秩序”(周文化原理層根基),也是孔孟傳承的“仁政”“仁禮”思想(操作層良性變異的成果)。具體而言,“守正”需做到三點:對“倫理秩序”,守“人際和諧、責任對等”的本質(如家庭中尊老愛幼、社會中誠信友善),而非“等級森嚴、絕對服從”的舊形式(如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的片面倫理);對“德治民本”,守“以民為中心”的本質(如關注民生需求、保障民眾權利),而非“君為主體、民為客體”的舊形式(如“君父愛民”的父權主義邏輯);對“禮樂文明”,守“以文化人、凝聚共識”的本質(如用文化涵養道德、用藝術傳遞價值),而非“儀式繁瑣、身份區隔”的舊形式(如貴族專屬的禮儀規范)。
2. “創新”:重構操作層的現代表達,讓原理層融入當代生活
激活“德治民本”:將其轉化為“公共服務倫理”(如政務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、民生政策“問計于民”)、“企業社會責任”(如關注員工權益、推動綠色發展),讓“以民為本”從“歷史理念”變為“可感知的實踐”;轉化“倫理秩序”:將其融入“社會公德”(如公共場合文明出行、網絡空間理性發言)、“職業倫理”(如醫生救死扶傷、教師教書育人),讓“倫理約束”從“傳統教條”變為“現代公民的自覺選擇”;煥新“禮樂文明”:將其融入“公共美育”(如博物館展覽、民樂進校園)、“社區文化”(如鄰里節、傳統節日創新慶祝),讓“禮樂教化”從“貴族專屬”變為“全民共享的文化滋養”。
周文化基因的傳承史已然證明:文明的偉大不在于“固步自封守形式”,而在于“守正創新活內核”。“原理層內核恒定—操作層實踐迭代”的機制,不僅為理解中華文明“延綿不絕而不僵化”的韌性提供了鑰匙,更可為世界范圍內古老文明的現代轉型提供啟示——唯有守住核心價值的“不變之魂”,創新實踐形式的“應變之形”,才能讓文明在時代變遷的驚濤駭浪中,既得以存續,更能煥發新的生機與光彩。(文/黨雙忍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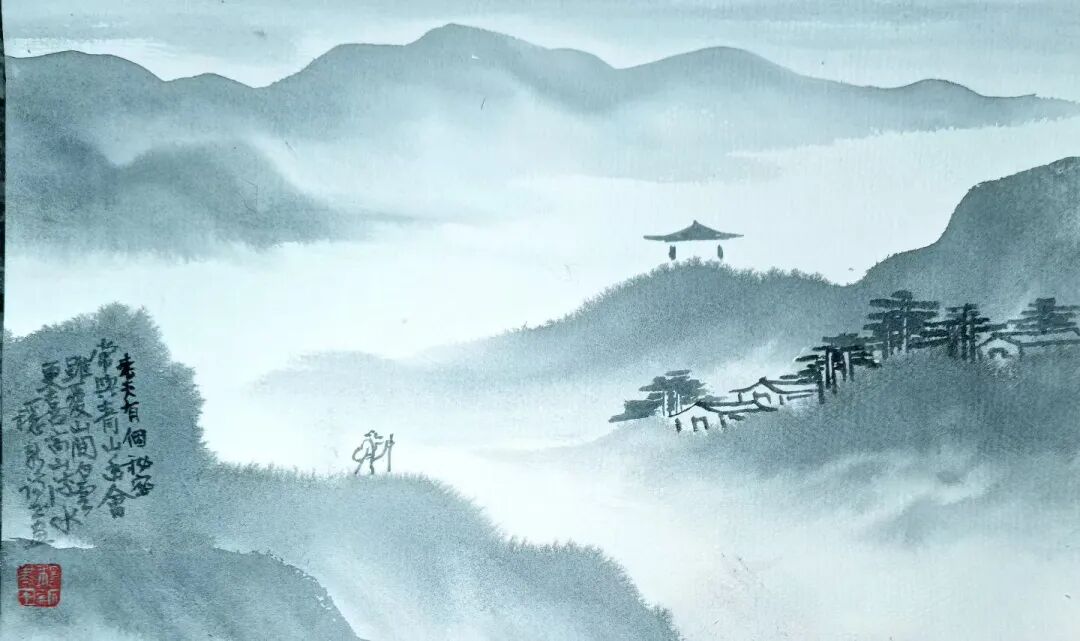

參考文獻
[1] 楊伯峻. 論語譯注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0.
[2] 焦循. 孟子正義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7.
[3] 董仲舒. 春秋繁露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75.
[4] 黎靖德. 朱子語類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6.
[5] 孔安國傳, 孔穎達疏. 尚書正義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0.
[6]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. 殷周金文集成(修訂增補本)[M]. 北京: 中華書局, 2007: 大盂鼎銘文(集成02837)、逨盤銘文(集成02819).
[7] 張載. 張載集[M]. 章錫琛, 點校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78.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