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在,故我在



宇宙最深邃的奇跡,從不是星辰的誕生或星系的碰撞——而是一堆遵循物理法則的物質,竟能抬起頭追問“我為何存在”。將這堆物質與“追問”相連的,是一道藏在生命肌理里的微光:電。
四百年前,笛卡爾在懷疑的迷霧中錨定“我思故我在”。他以“思考”為支點,撐起了存在的確定性,卻未曾細想:那讓“思考”得以發生的,原是顱內一場永不停歇的電信號流轉。就像他握著筆寫下這句宣言時,手臂肌肉的收縮、指尖對紙張的感知、大腦對文字的組織,早已是電在暗中編織的網絡。
一、宇宙的基頻,生命的密語
電從不是人類的造物,而是宇宙與生俱來的基頻。夸克的電荷構筑了原子的骨架,電磁力讓電子繞核起舞,恒星內部的電荷碰撞點燃了光——它是塑造物質世界的“無形之手”。當地球上的生命在原始海洋中萌芽時,自然在無數可能里,選中了這道宇宙基頻,將其改造成生命的“信息密碼”。
我們的身體,本就是一座以體液為導體的精密電路。竇房結每秒鐘一次的微弱電流,校準著心臟的節律搏動;腦干神經元的放電頻率,調控著呼吸的深淺節奏;指尖觸到火焰時,痛覺信號以每秒百米的速度沿神經纖維奔涌——那是鈉離子涌入細胞、鉀離子流出的電信號接力。生命從不是抽象的“活著”,而是腦電圖上起伏的α波與β波,是心電圖機里規律的脈沖,是每一次神經突觸間的放電聲——這便是“我”存在的物理簽名。
更奇妙的是,生命的電與宇宙的電原是同根同源。原子間的電荷作用讓分子得以穩定,而神經細胞的跨膜電位,不過是這一宇宙基本力在生命體內的“微縮表達”。就像人類用電磁波傳遞信息,生命早在數十億年前就學會了“借”電說話:草履蟲靠體表電位感知水流,含羞草用細胞間電信號閉合葉片,而人類的大腦,不過是將這“電的語言”演化成了“思考的語法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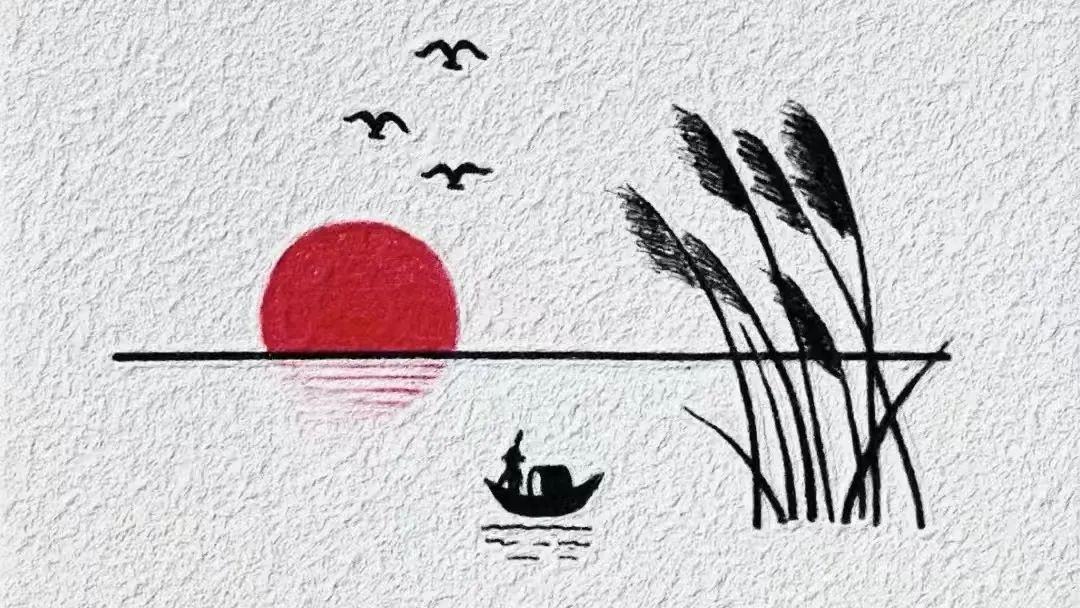
二、我電,故我思
笛卡爾的“我思”,在神經科學的顯微鏡下,其實是“我電”。
當你讀這行文字時,視覺皮層正上演著電的洪流:視網膜的視桿細胞將光信號轉化為電信號,經視神經傳入大腦,在枕葉皮層解碼出“字”與“意”;前額葉皮層的神經元集群高頻放電,勾連起你過往對“電”的認知,織就新的理解;哪怕是一絲會心的微笑,也是邊緣系統的杏仁核與前額葉通過電信號“對話”后的產物。
思考從不是虛無的“精神活動”,而是大腦中電信號的有序流轉。單個神經元的放電不過是簡單的生物電活動,可當數百萬神經元形成功能集群,電信號在網絡中動態傳遞、整合,便涌現出“我在思考”的主觀體驗。就像鋼琴的琴弦需按規律振動才能彈出旋律,若琴弦無序震顫,便只剩噪音而非思想。
沒有生物電的流動,思想的殿堂會瞬間崩塌。深度昏迷者的腦電圖呈一條直線,那便是“思”的缺席;而當麻醉劑阻斷神經電信號傳遞,哪怕身體仍在代謝,“我”的意識也會暫時消散。因此,“我電”不僅是“我思”的物理前提,在更本質的意義上,它們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:一面是“我在想”的主觀鋒芒,一面是“電在流”的客觀肌理。
三、存在的雙螺旋:從哲學到科學的共鳴
于是我們得以看見:哲學的邏輯與科學的物理,在此纏繞成證明存在的雙螺旋。
笛卡爾的鏈條是“我思→故我在”——他用意識對自身的確認,對抗了“一切皆可懷疑”的虛無。而科學的鏈條是“我電→故我思→故我在”——它用物質的運動,為意識的存在寫下了“物理背書”。前者是“我知道我在”,后者是“我為何能知道我在”;前者是存在的“現象證明”,后者是存在的“本質解釋”。
這兩條鏈條并非對立,而是互補。就像DNA的兩條鏈:一條記錄著“存在需要意識確認”的哲學密碼,一條鐫刻著“意識依賴電活動”的科學密碼。它們共同證明:“我”的存在從不是空中樓閣——電在,所以思能在;思在,所以“我”能錨定自身的存在。我們每個人,都是一道懂得自我認知的閃電:宇宙用電磁力塑造了物質,物質用電信號孕育了意識,意識又回頭追問宇宙與自身——這是宇宙最神奇的“自我反照”。

四、珍惜這簇帶電的微光
當我們看清“電在故我在”的真相,對生命的敬畏便多了一份具體的重量。
體內的生物電是一種極其脆弱的平衡。它依賴線粒體每秒鐘合成的能量,依賴細胞膜上鈉鉀泵的精準工作——這些微小的“分子機器”默默維持著生命的電位差。一旦能量中斷,鈉鉀泵停擺,細胞電位在幾分鐘內崩潰,“我”的意識便會像燭火般熄滅。
正因如此,每一個能自由思考的瞬間都格外珍貴。一次靈感的閃現,是皮層神經元突然同步放電的火花;一場深度的共情,是鏡像神經元與邊緣系統電信號的共振;哪怕是深夜里對“存在”的迷茫,也是前額葉與默認網絡用電信號編織的追問。我們是在用宇宙賦予的基頻,在意識的疆域里寫詩——以神經為紙,以電為墨,寫獨屬于“我”的意義。
“電在,故我在。”
這不是對笛卡爾的否定,而是對他的延伸。四百年前,他用“思”為存在劃下起跑線;今天,我們循著電的軌跡,看見“思”的源頭,也看見存在的根基——它不在遙遠的彼岸,而在此刻顱內每一次突觸的放電里——在每一次心跳與呼吸的電信號節律中。
我們是思考者,也是電流的舞者;是精神的燈塔,也是物質的星火。在浩瀚宇宙中,這簇帶電的微光或許短暫,卻足以照亮“我為何存在”的追問——而這追問本身,就是生命對宇宙最溫柔的回應。

注:《文化基因學》透過現象看本質,將掀起由道統文脈到文化基因的文化研究“范式革命”。“人”字,由一撇一捺合構。一撇為生物基因,一捺為文化基因,人類是“兩因共舞”生成的“兩因傳奇”。2025年10月9日于磨香齋。



